
5
·12那场震撼世界,让人撕心裂肺的地震正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灾区人们的生活是否恢复以往的平静?春节,在这最喜庆的日子里,他们生活怎样,脸上是不是挂着自信的笑容?带着这样那样的不解,在2009年1月22日(春节前三天)朝着那片曾经引起世人关注的土地奔去!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,在24号凌晨到了离地震震中最近的大站——绵阳。当时想等到天亮去汶川看看,绵阳的路人说北川是最严重的,我在一家站前旅馆歇息到了天亮,又乘大巴车去了北川县。
出了绵阳城区看路的两边随处可见地震留下的残垣断壁,和在建的新房。在大巴车上的时候心里也没谱,不知要去哪里,也不知第二天会不会拍到灾民过年的情景。我就和刚上车的人们聊天,后来就厚着脸皮要拍一个小伙子家里,要跟他回去过年,小伙子居然爽快地答应啦。
大巴车行至北川擂鼓镇就不走啦,我们在镇上看到年货还算丰盛,水果、鞭炮、腊肉什么的都有,只是蔬菜品种少些,而且水果有些贵。我和那个叫王俊的小伙租了一个面包车上山了,去了他们家。
他的家里还住的是帐蓬,就是蓝塑料布的那种,做饭的地方是自建的棚子,下面是用废砖砌起,四角用木杆支起,屋顶用塑料布覆盖。我们到时候男主人(王俊的爸爸)还在打豆子,王俊的妈妈开始做饭啦,炖豆腐和腊肉……
午饭后拍了一下孩子们游戏、唱歌的情景,又拍了一些采访。

小女孩刚吃完面

主人家的灶台,也是我们的午饭在上面

男主人在饭后沉思
那里的山很高也全是暗绿色的,从山顶一直铺到山脚,山上有南竹还有松树,在帐蓬外面也能看到叫不上名字又是彩色羽毛的小鸟。
村子里的其他人无事的有的在打牌;有的还在准备年后建房,在废墟里捡砖头出来。其中一位大哥说,过年啦,我家也没贴春联,也没什么可准备的,在篷子里住年就随便一点啦,盖房还差不少钱呢?!
后来听说,在当地盖一栋房子要十至十五万,政府可有一万多元的补贴,可有5万元的贷款(3年无息,5-8年还清),剩下不够的自己想办法嘞。
当天晚上我因着凉而发烧了,男主人王叔骑着摩托车给我找来了一些感冒药,有村医自配的药,用小纸片包着,还有板蓝根冲剂,晚上又喝了点去寒的白酒,十点多就在另一个帐蓬里睡下啦。说实在的,大冬天的任何取暖都没有的屋子,我有二十年没住过啦,盖两个被子,不敢脱衣服睡,还是觉得冻脸……一觉醒来,感冒居然好啦。
大年三十的早上还是小鸟、公鸡们轮翻欢唱唤醒了我,起来洗涑后,女主人开始做早饭啦,早饭是汤圆。昨天一直在吃面的小姑娘依旧端着面碗进来,只是面碗里多了几条肉丝,吃饭时,大伙围在灶台旁的火盆坐下,浓烟升腾,薰着吊在屋顶的腊肉。吃饭时又进来几个孩子,女主人拿出几个气球给他们玩,孩子高兴得不得了……
早饭后,我和王俊下山去镇上。镇上都是板房区,比山上暖和也热闹,我们到镇上时已经中午啦,随便推开几个住户,他们都在准备午饭,每家里都挂着不少腊肉,年货准备得不少,有的在炖鸡有的在炒菜,他们对我这样的外人也很热情,也约我吃饭,我一直不好意思吃,老乡们都不愿再提及过去,都表示对未来有信心,他们说只是永久性住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,春节后会建成一片廉租房,目前孩子上学不用花钱。采访结束后,我本想留在镇上拍一下羌族人跳锅庄,王叔派人骑摩托车接我们回去吃饭,扭不过就只得又回吃午饭啦。午饭比较丰盛,有王俊的姥爷还有他的姨夫们也在,不胜酒力的我,一杯白酒过后就到外面转向找北去啦。

刚下山的路上,脚下都是废墟

羌族卖腊肉人
下午去了同村(盖头村)的另一个组给王叔买些酒和鞭炮什么的。我们走的小路,路边都是茶树地,还经过一个引水渠,全村的人都是用这个水渠的水。同去的孩子说家里不给买烟花,对过年放花炮特感兴趣。回来的路上,他们一会儿放一个一会放一个,好在买的多,还有大半可以留在晚上放。
大年三十的晚饭就是中午的剩饭,菜也只有肉。简单把米饭吃下,不多时有孩子说他们要跳舞让我拿摄像机去拍,我过去啦。到哪儿一看,大家在几个帐蓬中间在空地上点起了火堆,只等那音响从帐蓬里接出来,只可惜线不够长,接不出来,最后还是把音响拿到了外面找了一个接线板。这时会跳舞的其实也就几个小学生而己,大人们大多不会,学生跳舞也是必修课,在课间操就是跳锅庄。
场面很乱,一半会儿也组织不起来,我的话他们也听不太懂,喊了半天才围在火堆外面,跳起并不整齐的舞蹈。我是里面拍,外面拍,被火堆的烟呛得不行。他们一直也跳不齐,这时有人说要再找几个学生来,我把现有的跳得还行的孩子叫到一边,把不会跳的分成组,由一个会跳的孩子来教。再跳起来就齐多了,后来大伙都累啦说要回去,我让几个会唱歌的女孩子给大家唱歌,让村民们在一旁鼓掌。活动一直进行到快十二点啦,《春节晚会》也没看到,不过和他们在一起也挺开心的。
大年初一的早上还是汤圆,因为没什么味道,就从泡椒凤爪里夹几个泡椒吃。吃过早饭就下山啦,去了曲山镇,王俊的二姨夫家,因为那里是进入北川县城的入口,他有当地的身份证,如果可以,能把我带进那座废城。
在快进入曲山镇的时候不是本地人都要下车,因为王俊的二姨夫朱先明是曲山镇户口,我们的摩托车直接开到了山上板房区家里,这里很热闹,有本地人也有外来的游客,每天上山的人络绎不绝,有数万人之多。
这里的每一排板房都有厨房、水房,每几排板房有一个公厕,板房区有卫生所、邮局、超市、储蓄所等,设施可谓完善。不过这里将来要被拆掉变成旅游区,灾民们还不知去向何方?

板房区外景
板房区家家户户都贴春联,春联是一些企业赞助送的,有企业标识的,门上面很多都挂着胡主席和温总理查看灾情时的照片,他们心中非常感谢中央政府、全国人民和所有帮助过他们的志愿者,只是对当地政府印象不太好。在吃午饭的时候录了一段向家里拜年的视频,当然家里也看不到,只是录下当时对父母和在京的朋友们怀念的心情。饭后我去了北川中学,随后向县城方向走,县城已经被封住啦,我没有县城里的身份证当然也是进不去的,就是记者也要有介绍信,记者证都不行。我只能随着人群上山,从山上俯看县城,很多在县城有亲人的也有的是素不相识的人,向遇难者烧香凭吊。

为县城死难者上香

北川中学大门外

废墟外面用铁栅栏围住,只能远观
晚上,是在朱先明在妈妈家里吃的,也是一大家人,我有些不太习惯。饭后,外面响起来锅庄,我想去学学,就一起跟着跳。上身手的变化还能跟上,下边的脚就不会动。一曲锅庄有五节,每节变化不同,哎,我没学会。
初二,阴雨绵绵,天气不好,朱先明去了他木匠师傅那里,师傅要给他说一门亲事,因为他爱人在地震中去逝啦,还怀着孩子。
我在他家中呆了一天,晚上照旧去跳锅庄……

在右三婆婆的儿子家住过一夜
初三的早上,外面传来吵嚷之声,循声过去,原来人群中在发东西,所有人都把手伸向一个扎两个辫子、头戴黑线帽的女孩子,她一边发一边喊,“别急还有啊”。发的东西品种不少,有药品、小点心、手套、防冻膏还有袜子之类,同来的还有两个男生,一个是《南方周刊》的记者,另一个是志愿者(曾在这里教过孩子英语)。事后采访了那个分发礼物的女孩子。原来,她是贵州人,从老家买的礼物快递至成都,再从成都赶来北川,在听说她回成都后,将要去地震伤员康复中心时,我也萌生要去看看的想法。后来他们先返回成都了,我是第二天(初四)离开北川的……

志愿者与学生在一起

与骑摩托送我下山的大姐留念
在北川的印象是:灾民很乐观,他们知道感恩,对总理和主席特别感激,他们年后大多又要去外地打工,希望在政府的扶持下早日重建家园。那里有的板房区要被迁到彭州去,留下来的板房人家也不知未来会怎样?他们的心态是乐观的,在经历了这场大地震后,他们更注重亲情,人与人之间显得那么和睦,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,相信一定会有出路的。年后他们又将去往全国各地打工挣钱,改变现状,重新在废墟里站起来,建起不会倒塌的家园……(未完待续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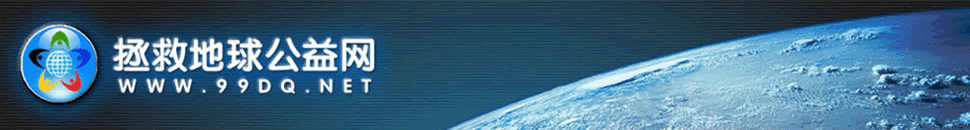

 看完一些文字后 你真得很棒 这是件大好事
看完一些文字后 你真得很棒 这是件大好事
 有理想的青年人呢
有理想的青年人呢
 还记的我不哦。王俊,我QQ272648255
还记的我不哦。王俊,我QQ272648255